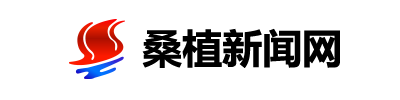
桑植融媒5月18日讯(通讯员 廖诗凤)这里的老街和所有的老街一样,也在安静中孕育着情怀。几间保留尚好的四合井院,几间破败欲倒的四合井院,几间不伦不类的矮木房和一条时断时续的石板路,镶嵌在万千繁华里,像极了海滨广场上的一艘简单的木船雕塑。
这便是桑植县城文昌街有着四百多年历史的老街了。这残存下来的老街不长,长不足百米;老街也不宽,宽也只能盈丈。和澧水河畔的苦竹古寨比,苦竹古寨要幽深曲折多了;和沅水河畔的凤凰古镇比,凤凰古镇要大气磅礴多了;和北海的老街比,北海老街便是海,文昌街的老街便是沙子了。
说起来真有点伤感了。但如果能够亲自在这条老街上来回走一走,听一听风过深巷的呜咽,听一听石板从脚下传出来的共鸣,听一听那些悬挂在板壁上的在岁月剥蚀下瘦骨伶仃摇摇欲坠的苍老物件无声而又大声的喧哗;你也可以驻足下来,带着你的好奇和善意,轻轻推开那些虚掩的大门,带着你的谨慎,看看天光如何滋养瓦砾中的万物,看看阳光如何把每一个角落都照亮,看一看雨水又如何将一切都淋湿;你也可以带着好奇和善意,走进那些幽深的槽门,向蛰伏在里面的老人说明你的来意,然后,在不打扰老人的前提下,拿起你的相机去记录这里的曾经和过往。那么,你将不光是有点伤感,而是有点激动,有点莫名其妙的而又顺理成章地生出许多人文情怀来。
在一个小雨刚过,骄阳又出的晌午,我带着一丝莫名的冲动,撞进了这有着四百多年历史底蕴的袖珍老街。
我无需考证历史,更不想借用典故,我只想凭借我自己的眼睛和肌肤的感触,独自去触摸小街的存在,去感触那些还未被挖掘过的故事,去发现和探究我自己想要的又符合历史的东西。
我说是撞进,其实用“挤进”一词会更加准确。这里四百年的时光包浆太过厚重,要想真正地进去,不挤一挤,那一定是走马观花、隔岸观火了。其实,我此前也查阅了许多关于桑植的历史文献,知道桑植的存在也远在洪荒。人类能够记录的历史其实也只是历史长河中的沧海一粟,仓颉造字都是上古,都是神话,人类的进化和演变,不是一个典故,一个藏本,一个传说,一个记载就能甄别和肯定的。道听途说,无中生有,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真实的存在,更何况改朝换代,历史的记录也会变换颜色,那些资料也是时代的产物,统治的工具。当然,我查阅资料并不是要带着这些资料去说教,而是想把这些资料当作我识海破境的法宝,在自我的吸收和炼化中感悟苍天的力道,完成自我对物象的感知和情怀的升华。其实,就我的知识,还不能达到引经据典,信手拈来名家名言的水平,无法炼化那些高深莫测而又虚无缥缈的文史记载。
从文昌街自东向西靠左缓步探寻,便寻得一老面馆,临街一面仿宋酒旗迎风正在飘动,颇有几分老旧姿色。见色起意,我便大步挤进去,向面小二要了一碗桑植“老面”,然后拿着我的相机肆意地拍起了老砖老土来。桑植“老面”果然有点老,一碗面下肚,我便感觉自己的识海又老了几个春秋。
接下来的探寻,吸引我的就不再是眼球,而是心扉。
我的眼球瞬间被一个颇有特色的石头槽门所吸引。石槽门高约一丈,六尺通人,湘西石碑状兀立。前有石阶三级,象征富贵登科。槽门石柱上有块石牌,阳刻着诸神几位,祥云几朵,两根石柱上阴刻着对联,可惜时代久远,被剥蚀得无法辨认。我怀着虔诚轻轻推开虚掩的两扇大木门,轻轻地走进了百年老宅,一睹她的芳容。
扑入我眼帘的是沧桑和凌乱,是激动和震撼。我小心地迈过九寸高的石门栏,顺势用手抚摸了百年老墙,感觉就有一股强大的气息带动着我的气海,一阵翻腾。我踩在满是绿苔的泥地上,就感觉自己已经穿越了洪荒,来到了一个满是法宝的境地。
房屋保持良好,标准的桑植四合井院子,两层吊脚,天窗地井,通天纳气。雨才过,井中有浅水,映着天上日,金光摇曳,万道祥光入我眼来,我也感觉如出大境。
正在忙碌的两个老人,或许司空见惯了这般打扰,并没有过多地对我理会,但我还是简短地说明来意,并一再表示“抱歉。打扰。”我知道,他们都是这方世界的修仙之人,早已忘记了时间和自己,我也不能让我的唐突惊扰了他们的清修。当我转身的瞬间,却又被眼前的破败把心戳得很疼。
我迫不及待地要寻找些许安慰,便急步走向已经有文友写过的文昌老街。
文昌街的小街,他的一半已经向后转了,以华丽的姿态转世,投胎在新的文昌街了,只把他尚不惊世的背面留给他朝夕相处的另一半。遗憾的是身在另一个世界里的另一半,也正在被新的东西蚕食、感染,变得不伦不类,面目全非。
让我意料之外的是,这里还保存了一座较为完美的四合井院子,可惜的是石头槽门已被毁了,但三步石阶依旧,木制拱门高大,也颇有几分气势,只是少了些许苍老。值得欣喜的是这家院子生活气息很浓,炊烟不断向天窗飘去,瞬间虚无。天井聚水纳财,几只乌龟正在天养。虽是四合井院,却能凭一方天窗得到充足的光亮,从一楼到二楼,都浸泡在温柔的明亮之中。
我的款步,这次却惊动了里面的两个老人,在我的自言自语中,他们转身邀我入座,并送来了滚热的桑植白茶。白茶氤氲,奇香扑鼻。
和主人的聊天中得知这座四合井院实乃张氏祠堂,重修方才百年。难怪凡气浓厚,法器新致干净。两个老人也精神矍铄,心胸开阔,热情好客,传承了桑植土著民的美德,活得喜庆。
一百年的历史于我这个花甲之人还不是大的气场,我要找的是能释放四百年历史能量的法器。我走出这一百年的气场,便继续拐进了另一个深巷。
这一次,又一个有着高大石槽门的四合井院子出现在我的视线里,结构和东门的雷同,只是比东门得更加破败,已经一半坍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天窗。天井早已被瓦砾覆盖,荒草萋萋,满目疮痍。正楼早已摇摇欲坠,只留下一个横房住着一个老人。老人睡着老式木质牙床,扎染铺盖,苎麻织成的蚊帐,古色古香。不知道这是老人的偏执,还是老人的情怀,还是别有什么更加深层次的含义。果然,和老人的交流中,让我捕捉到了一丝天机。原来,老人如今所睡的房间,曾经是驻防桑植的湘西护法军第一营营长贺龙的卧室。青年贺龙在这里处理军务,批示文告,劳心劳力,睡的就是这样的牙床,这样的被子和这样的蚊帐。也不知老人的话是真是伪,或许也是听老辈人传说,但是,从他的修仙中却充满了对贺龙元帅的敬仰和膜拜,更是想传承贺龙元帅的那种情怀。
是啊,我曾翻阅过《贺龙传》,里面记载了1918年22岁的湘西护法军贺龙营长全面驻防桑植。驻防期间,赈济灾民,打通乌龟嘴通往外界的阻路,将泥泞坡陡的一段改成128级台阶的石板路。青年贺龙这种爱民爱家的情怀,正是他后来戎马一生,鞠躬尽瘁为国为民的深厚铺垫。
听老人说,他现在所住的房子和东门那个一样的四合井院子主人的后嗣如今都居住在美国,过着殷实的日子,中国大陆和海岛融洽的时候,他们的后人带着他们的洋媳妇还回来认过祖屋,拍了几张照片后便一步三回头地走了。从此,这两个四合井院子与主人天各一方,两相牵挂。
留守在这里的老人,说有石槽门的院子都有了两百年以上的年龄,除了地上的被磨得如砥般的石头和那些捏得出汗水的红色泥土能承载更加悠远的岁月,那么这些老院子,这条老街,就承载起了近代历史的千年经典。
我走出这条袖珍老街,又想起“文昌”两字,这才顿悟它的深刻含义。古老的桑植住民和客家人,在他们的心里一直崇尚文运,他们在这里办学堂,建书院,修圣庙,就是想以文治家,以圣修邦,让天地达音,让邦临和谐。“文昌”一词,便是文运昌达,“文昌书院”也便是赋予这条老街的最初情怀。 难怪几百年来,桑植出了那么多达官显贵,那么多儒道学究,那么多乡贤绅士,这与桑植人对“文昌”的炼化具有千丝万缕的关联。
我想桑植人一定希望这条老街能保留下来,而且还能得到修复,还原“文昌书院”,还原“文殊庙”,还原这条老街的繁荣和古朴,让远在他乡的游子有根可牵,让桑植后人有历史可鉴,就像北京的那些老胡同一样,于万千繁华中彰显出他与众不同的无限魅力。
责编:张思
来源:桑植县融媒体中心

版权作品,未经授权严禁转载。经授权后,转载须注明来源、原标题、著作者名,不得变更核心内容。
!/ignore-error/1&pid=52087955 )
全县各界收听收看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实况直播
!/ignore-error/1&pid=52030490 )
县政府月度例会丨梁高武:凝心聚力 真抓实干 以务实作风推动高质量发展
!/ignore-error/1&pid=51962010 )
曹飞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2025年第21次会议
!/ignore-error/1&pid=51962000 )
桑植县召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进会
!/ignore-error/1&pid=51961655 )
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2025年第8次集中学习举行
!/ignore-error/1&pid=51961990 )
桑植县民族团结进步标识LOGO、IP动漫卡通形象和主题歌盛大发布
!/ignore-error/1&pid=51933165 )
梁高武主持召开桑植县第十八届人民政府第88次常务会议
!/ignore-error/1&pid=51813870 )
桑植县2025年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
!/ignore-error/1 )
伴随着桑植的万物生长,打开脑洞,你还知道哪些桑植的“野生”汉字?#歌里画里桑植等你
!/ignore-error/1 )
千年赶一街,一街赶千年。芙蓉桥第十届“三月街”等你来相会!感受桑植民俗文化#民俗文化 #歌里画里桑植等你
!/ignore-error/1 )
是谁,送你来到大桑植 #桑植白茶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乡村振兴 #歌里画里桑植等你
!/ignore-error/1 )
张家界桑植芙蓉街第十届“三月街”等你来#歌里画里桑植等你 #民俗文化
!/ignore-error/1 )
清明祭祀请牢记!桑植方言版森林防火口诀!#森林防火#全民参与
!/ignore-error/1 )
15分钟×4万学生=?桑植县用课间改革交出活力答案
!/ignore-error/1 )
冲刺高考 桑植一中学子开启逐梦新篇
!/ignore-error/1 )
记河口乡沙洲村支部书记陈仙娥的奉献之路

下载APP



